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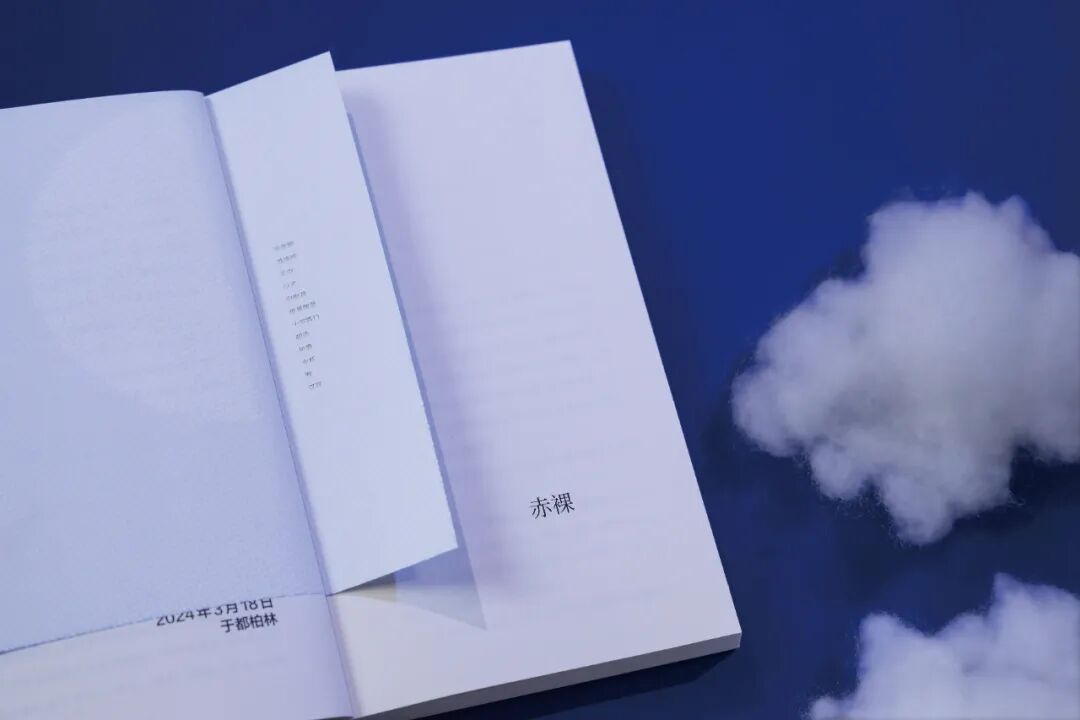
“有一次看卡夫卡的日记,他说他有一种睡眠崇拜,因为他也是睡不好觉,所以对能睡好觉的人有一种崇拜。我也是这样,我是一个受失眠困扰极深的人,非常渴望大眠。我不仅崇拜能睡好觉的人,还崇拜对这个世界不过分反应的人。有时候你在创作状态中会打开所有的毛孔,这会让你这个人变得极度敏感。但是你就是得把它张开,因为只有在张开的情况下,整个字词才是能够呼吸的状态。”这是青年作家杨好在与清华大学教授、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的对谈中,谈到的自己对于“睡眠与写作”的观察。
曾有人将失眠描述为“白天心事的种子,总在夜里开花”。人之所以会失眠,往往是困于繁琐的日常中,内心总有一种“无法把握生活”的焦虑。但正如格非在对谈中说的:这个世界你根本没法把握,我们人人都是如此。近期,围绕杨好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大眠》,格非与杨好就“文学与世界以及自我的关系”,展开了一次深入对谈。

杨好×格非
真实生活 如同梦境
格非
清华大学教授;茅盾文学奖得主
杨好
作家,生于山西,长在北京。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比较文学博士。曾出版艺术史作品《细读文艺复兴》,长篇小说作品《黑色小说》《男孩们》。《黑色小说》入围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
在波兰作家卡普希钦斯基《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一书的中文版封面上,有一行并不醒目的字,写着:我们在历史记载中遇到的事情,和自以为在这个时代可以躲开的事情,完全相同。而作家杨好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大眠》所要讲述的,也正是这个主题: 面对真正的意外,我们漫不经心。
文学艺术,有何必要?
格非: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曾经问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他说这个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我们人作为感知的主体拥有一个世界,比如说是外面的广场、街道、森林、江河、湖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客体,需要主体来认知这个世界。你想了解这个世界,了解其中的奥秘,就得把自己投身到这个世界当中去。
列维纳斯的问题是,人类为什么会发明出一种东西叫“文学艺术”,这有何必要?文学艺术,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它是对生活的模拟,它本身是不存在的。本来也不需要这个东西,只需要我和对象就可以——比方说,外面刮风了我觉得这个风很好听,下雨了,我觉得雨声很好听,鸟鸣很好听,花很好看,这就可以了。为什么我要画一幅画,它的必要性是什么?
列维纳斯没有正面解答这个问题。我的解释是:当文学和艺术模拟这个世界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叫美。美需要一个距离,这个距离需要通过一个中间物来抵达。需要一个时间距离产生,比如十年以后、五年以后我想起这个场景的时候,有了距离感,也就有了美。当文学在模拟这个世界的悲欢离合的时候,就与生活产生了距离。这种距离感一方面会产生美,同时也让我们从生活的严酷中逃离。
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遇到一件事,对我产生直接的困扰,让我很难受,我们往往也需要通过写作,让事件本身产生距离。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这种从事件中逃离的功能。文学有两种描摹方式。一种是把生活中的困扰,通过模拟让自己获得自由,这是文学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不要忘了,文学还会模拟我们的情绪。杨好的《大眠》里很多作品都在模拟这个情感,这个东西捕捉不到,不是具体的事件,就是情绪、情感、困扰、烦恼,那种不能很快拒之门外的东西。通过模拟这个情绪和情感,让它和自己保持一个距离,从而可以观照它,把握它,这是写作非常重要的意义所在。如果有朋友愿意写作的话,你写到后来会发现,你在脑子里思考一个问题,跟你用笔来描摹这个事情,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我们说写短篇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比长篇困难得多,那是因为,短篇小说所要模拟的情感更加细微幽深。
杨好:格非老师谈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情感”或者说“感觉”,雷蒙·威廉斯曾经提出过一个理论,叫感受的结构。他说在大多数时候,在文学中写的不是那种已经被定型的或者已经被确认的东西,更多时候是在捕捉一些还没有定型的东西,这些还没有被定型的东西就是时代的气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中,这些东西像空气一样裹挟着我们,它是漂浮的,不确定的,是没有被定型的。我想文学有一部分的工作就是在捕捉这样的感受,就像我在《半衰期》里面写到深海中埋藏的炸弹一样。
我想这可能是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现实永远是关乎真实的事实,但是文学可能更多的是关乎一种内心的事实,这个事实可能不是真实的,但它是诚实的,你在写作中能够找到这种诚实。只有在文学创造的空间里,能宽容这种不确定的、有些飘忽,同时有时候又极度危险的东西。我上个月看到英国的一个新闻,说在城市的一个超市里,突然发现二战时期遗留的炸弹。我在想,这不是我《半衰期》里写到的事情吗?所以真实和想象的边界在很多时候是模糊的,甚至这个边界是颠倒的。也许你做的梦就是最现实的东西,也许你身处的现实反而是一场梦幻。
经常失眠的作家
都有“睡眠崇拜”?
格非:我在读杨好作品的时候,尤其在读第二遍时,会读出很多原来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有些意象意味深长。我跟杨好年龄相差很大,生活经历相差也非常大,我就会好奇杨好为什么处理的那些人都是影影绰绰的,没有分量,像影子一样飘着?比如说这个人物家住什么地方、什么职业、什么性格、每个月挣多少钱、有什么烦恼,这些东西都没有。那这个人,你说他不真实吗?也不见得。我对这些看似飘忽不定的东西很着迷,因为我觉得这正是他们这代年轻人眼中所看到的世界。
杨好:格非老师说我的好多人物“影影绰绰”,这个词非常准确。回忆写《大眠》的这三年,我通常都是在黑夜和白天交替的时间去写的,因为我是一个受失眠困扰极深的人,非常渴望大眠。有一次看卡夫卡的日记,他说他有一种睡眠崇拜,因为他也是睡不好觉,所以对能睡好觉的人有一种崇拜。我也是这样,我不仅崇拜能睡好觉的人,还崇拜对这个世界不过分反应的人。有时候你在创作状态中会打开所有的毛孔,打开所有毛孔会让你这个人变得极度敏感。其实这个过程不是写作带给你的那种痛苦,而是你打开写作状态,所有张开的毛孔带给你的那种生命的压力。你在这个期间会失眠,会过敏,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都是需要你扛过去的。但是你就是得把它张开,因为只有在张开的情况下整个字词才是能够呼吸的状态。
《大眠》里面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欲望的反射。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欲望的反射,让小说里的人全部变成飘浮的、不实的、影影绰绰的东西。我有一个理论课,讲的是勒内·基拉尔的“欲望三角”理论。在一遍一遍备课中,我发现他所说的三角是主体、客体加一个中间的中介,这个时代可能充满过多的中介,科技也好,媒体也好,都是离我们过近的中介。我们渴望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原始的欲望,不是我们原本渴望的东西,而是在渴望别人想要的东西。这个别人想要的东西通过这些中介的不断反射,形成无数次的镜像,在这个镜像中的人别说找不着自己,你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可能正是这些镜像组成了所谓影影绰绰的这些现实中幻影的一部分。
格非:语言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多不可捉摸的。我想写作的魅力往往就在于此。有时候我自己也有这个感觉。写完以后你重读自己写的东西时,还会觉得难以置信,会觉得那么陌生,沉浸在一种创造新事物的神秘体验当中。当然,有的时候你找不到这种感觉,也许一天两天,都找不到那种特别好的感觉,作家在这时候非常痛苦,他需要等待,需要耐心地找到那种感觉。所以,我反复强调,作家不一定能完全把控他写的每一个句。如果那样的话就不存在语言艺术,不存在文学。小说非常迷人的地方在于,即便你是富有经验的作家,有时候也不一定能把控你的作品。小说要比你伟大得多,作家的作品伟大不是因为作家本人伟大,而是因为创作把你代入到那个特殊的带有创造力的情境当中去。福柯当年说过一句话特别精彩,你写出一个漂亮的句子,你怎么知道是你写出来这个漂亮的句子,而不是一个漂亮的句子突然从你眼前飘过被你抓住?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创作状态可遇不可求,我们需要很好地调整自己,需要大量读书,需要不间断思考,这些训练会让这种状态得以出现。一个有训练的作家跟一个没有训练的作家是不一样的,好作家经过几十年的训练会让自己相对容易进入那种可遇不可求的状态。当我们去描摹这个世界时,并不是说所有东西都预先想好了,然后一字一句地写下来。写作所面对的情境要复杂得多,它固然是一种模拟,但同时也是一种开启和发现,一种出神入化。
杨好:我其实自己也在不停地回看《大眠》,很多时候这些文字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因为它们是在我没有准备的前提下写出来的,这个“没有准备”并不是没有做好写作准备,而是在我没有写出这样一个句子的时候它已经出来了。很多时候写作者会在非常“活生生”的状态下写作的,这个“活生生的状态”是一个不可预期的状态,因为很多时候你说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死去的状态,那种状态下你的字词是不生长的。
世界被拉平,
但人仍要快乐
杨好: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关于时代的定义,是否是模糊的?甚至是相反的呢?十年前,我非常相信这个世界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答案,所以我特别想成为文艺复兴人,我以为文艺复兴人是能够寻找到答案的祭司。我现在发现,这个世界完全变了,再回到原来一些地方的时候,你发现你看到的伦敦、纽约和北京,跟十年前全都不一样了,这个世界开始变成被拉平的东西。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们经历了全球化,但它一再被摧毁,被重建,被解体,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分崩离析,破碎不堪。但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负面的情况,反而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我好像慢慢开始听到自己的声音。对于写作者来说,只有作品能够定义自己是谁,时代的局限在你这儿是非常脆弱的。
格非:杨好现在在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读博。上学期她帮导师给研究生上课,讲鲍德里亚。我最近也看了很多鲍德里亚的作品,包括他去世之前的一系列访谈。我们之间有过一些交流。最近我也读了当年德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安德斯的作品《过时的人》。关于技术的问题,我和她也有一些讨论。尤其是今年春节以来 DeepSeek 出现后,我突然发现技术的更新迭代速度非常之快。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相信全世界会有一部分人跟我一样感到忧心忡忡。我们经常把人跟动物相比较,鲍德里亚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人跟动物完全不同。鲍德里亚认为,人发展技术的目的,不是为了拯救人,不是为了让人过得更好,而是为了把技术这个东西推向极致,人有一种对于技术无法克制的贪婪欲望,就是不断创造新技术的欲望。可是最近五年来,我们受到的影响已经非常吓人,比如我在清华做老师,不把学生手机全部收上来的话,就没有办法考试,因为没有什么问题是 DeepSeek 不能回答的。这个对人文学科的研究,甚至对文学的创作,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我认为这种技术在未来几年中会飞速发展,是可以想见的。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是AI 不能取代的?我想了半天,说只有一个东西不能取代,就是我们的生命体验。机器能取代的是知识的综合。知识是某种被固定化的东西,而我们对一个东西的感知能力和情感体验,这个东西是随时生成的。
我经常跟朋友聊这样的问题:一个人要获得快乐,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最高的条件和最低的条件是什么?我说的回答很简单。一个人只要能思考,有体验,快乐就不可能被剥夺。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机器不能取代的。所以我跟很多朋友也讲,就算 AI 将来写得比我好,它也不能剥夺我表达自身生命体验并从写作中获得快乐的权利。写作是我们的权利。从事创造性的、带有神秘性的工作时带给我们的快乐的权利,不是 AI 能剥夺的。
杨好:AI不能剥夺的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律令,就是康德所说的,它不能剥夺我们的是对天空、神明的敬畏,也不能剥夺我们自己对自己内心的谦虚和谦卑。AI可以模仿技术,但是这种敬畏和谦卑是永远无法被模仿的。
文 王雅静
编辑 韩哈哈
资料支持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史依弘 与京剧的百年对谈
王芊懿&王柳懿 “她”漾精彩
李娜 刚柔并济 逐冠人生
潘展乐:赛场上没有退路 只有拼到底
张雨霏 蝶变之后
王羽佳:探索不止 恒动不息
汪顺:年龄只是数字 实力说明一切
新 刊
「 2025年8月28日 景军 」
睿迎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